楼主 (北美华人网)
读史札记|从一位官员日记中窥见晚清社会风貌 王锺霖于嘉庆二十一年(1816)出生,山东济南历城人,为甲辰科(道光二十四年,1844年)的山东乡试举人。在咸丰八年六月,通过吏部选拔定岗之后,开始前往京城任职,此后的日记所载,大部分为在京任职期间的京城生活记录。日记的主要记载内容以日常生活为主,按记载内容,王锺霖主要活动区域有山东、直隶和京师一带。王锺霖先后在不同地方任职,每到一处,他都会细心观察当地的风俗民情,通过阅读他的日记,可以对晚清的世情风俗有更加清楚的了解。 外来人口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情况 王锺霖记录了在京城内生活的情况。咸丰十年五月廿九日载,“京中内外城官民所用甜水除自己有车自拉外,余皆水屋按时卖给,凡有水屋皆山东登州人,无论大风雨必须送到各门挨卖……京中居民不下百万家,皆仰给此车之水,亦多不肯得罪他,盖水屋各有分界,他处不能越送也。山东东三府在京贸易者,亦不知有多少人,若大京城,食水酒肉皆东人,各衙门轿夫皆东人,下及拾粪者亦是,其他煤炭、油盐、放小利(怅)[账],京中要事,山东、西人实掺大半,人云非山东、西人不能如此,辛勤性久能赊、能要也。京中大事之坏者,皆山西人放大小(怅)[账]者收本回家所致。”这段叙述中描述了外来人口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情况。 在北京工作的外省人大部分是山东、山西人,在各行各业中都有着他们的身影,在北京进行贸易来往的,也有很多山东人。甚至有部分工作只有山东人能够胜任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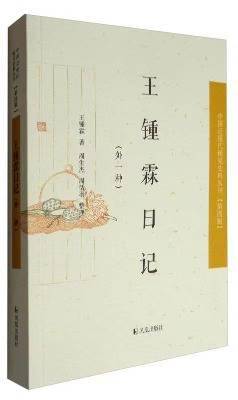 《王锺霖日记(外一种)》,王锺霖著,周生杰、周恬羽整理,凤凰出版社出版 缺水的北京 日记对当时北京的供水情况作了一个很详细的描写。自古以来,人类用水的源头主要来自雨水、地面水和地下水,最适合公共使用的水源为地面水,其次是地下水,最后是雨水,但雨水不稳定。除此之外,在地面水方面,也是缺乏的,“近郊二十里,无河流灌润”, 因此北京居民在日常用水方面较为依赖地下水,即井水。 北京人口稠密,用水量大,但是供水的措施并不发达。“北京的井多在街上,除了王公之家,极少在自家宅院凿井。街上水井系卖水者所有,故市人常自卖水者手中买水。”除了甜水井是自行用车去取之外,其余的井水都是通过水屋的工人去运输,按日记中叙述,经营水屋的均是山东登州人,送水的工作十分辛苦,需风雨无阻地送到各家,突出了山东人的辛勤。而水屋的经营范围也有明确的划分,不同水屋有着不同的送水范围,互不侵犯,这种分段经营的方式早在乾隆年间已经开始定下来。“从乡缘的角度,这种分段把持的经营方式,或许也是同乡之间彼此的互利措施,也就是山东人基于‘有饭大家吃’的乡谊,产生了这种联合垄断的方式。”通过日记可以看出,这种同乡情谊虽然是建立在利益之上,但是乡里有困难,水屋的其他同乡也会伸出援手,用平常积累下来的公款,帮助有需要的人,可以说是十分有人情味。 频繁变动的物价 晚清动荡不安,除了吏治败坏,在经济方面也十分不稳定,通过货币的浮动就可以看出。货币的价格浮动幅度非常大,而且速度很快,同一天的早晚银价就有所变动,可见晚清时期政府对于银价的控制十分薄弱,食物的价格高昂,换而言之就是百姓可能面临饥饿,而市井商人则从中获利,市场出现失衡。 经济不稳定的情况持续了一段长时间,王锺霖在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了银价波动的情况。咸丰十年(1860),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,百姓欲逃往其他地方避难,纷纷到钱铺取钱,部分私人钱庄的老板早已弃铺而逃,百姓只能到官号取钱,但官号储备金钱不够,只好能拖则拖。除了米面菜蔬这些必需品之外,衣物也已经不值钱,市道萧条,顾客稀少。除此之外,当铺也是货物满架,并且此时是有当无赎,因为当铺已经出不起高价,所以市民只好把自己的物件低价当给当铺。 战争和灾荒会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变成货币,用货币购买粮食,越来越多的贵金属流入市场,形成供大于求的情况,这样一来使得货币的需求增加,银价会下跌。由于太平军连续攻克了重要城市,如安庆、南京,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,因此就算是身处北京的居民也感到不安,金融恐慌也就发生,银价开始大幅度跌落。清廷为了筹集军费,除了下放赋税权力之外,也滥铸减重的小制钱,导致通货膨胀。 总结来说,日记中所记录的关于银钱兑换的情况,反映了咸丰时期的战争与银价的下跌有密切的关系,其次战争也破坏了当时的商品经济,使货币流通规律产生了变化。 《王锺霖日记》一书主要收录了王锺霖自咸丰八年到咸丰十一年的日记,从中可以窥见晚清社会风貌。 《王锺霖日记》中所载史事,多是作者细心观察之后的记录,史料价值很高,既可以证史,也可以补史,可以作为晚清历史研究的文献资料。
《王锺霖日记(外一种)》,王锺霖著,周生杰、周恬羽整理,凤凰出版社出版 缺水的北京 日记对当时北京的供水情况作了一个很详细的描写。自古以来,人类用水的源头主要来自雨水、地面水和地下水,最适合公共使用的水源为地面水,其次是地下水,最后是雨水,但雨水不稳定。除此之外,在地面水方面,也是缺乏的,“近郊二十里,无河流灌润”, 因此北京居民在日常用水方面较为依赖地下水,即井水。 北京人口稠密,用水量大,但是供水的措施并不发达。“北京的井多在街上,除了王公之家,极少在自家宅院凿井。街上水井系卖水者所有,故市人常自卖水者手中买水。”除了甜水井是自行用车去取之外,其余的井水都是通过水屋的工人去运输,按日记中叙述,经营水屋的均是山东登州人,送水的工作十分辛苦,需风雨无阻地送到各家,突出了山东人的辛勤。而水屋的经营范围也有明确的划分,不同水屋有着不同的送水范围,互不侵犯,这种分段经营的方式早在乾隆年间已经开始定下来。“从乡缘的角度,这种分段把持的经营方式,或许也是同乡之间彼此的互利措施,也就是山东人基于‘有饭大家吃’的乡谊,产生了这种联合垄断的方式。”通过日记可以看出,这种同乡情谊虽然是建立在利益之上,但是乡里有困难,水屋的其他同乡也会伸出援手,用平常积累下来的公款,帮助有需要的人,可以说是十分有人情味。 频繁变动的物价 晚清动荡不安,除了吏治败坏,在经济方面也十分不稳定,通过货币的浮动就可以看出。货币的价格浮动幅度非常大,而且速度很快,同一天的早晚银价就有所变动,可见晚清时期政府对于银价的控制十分薄弱,食物的价格高昂,换而言之就是百姓可能面临饥饿,而市井商人则从中获利,市场出现失衡。 经济不稳定的情况持续了一段长时间,王锺霖在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了银价波动的情况。咸丰十年(1860),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,百姓欲逃往其他地方避难,纷纷到钱铺取钱,部分私人钱庄的老板早已弃铺而逃,百姓只能到官号取钱,但官号储备金钱不够,只好能拖则拖。除了米面菜蔬这些必需品之外,衣物也已经不值钱,市道萧条,顾客稀少。除此之外,当铺也是货物满架,并且此时是有当无赎,因为当铺已经出不起高价,所以市民只好把自己的物件低价当给当铺。 战争和灾荒会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变成货币,用货币购买粮食,越来越多的贵金属流入市场,形成供大于求的情况,这样一来使得货币的需求增加,银价会下跌。由于太平军连续攻克了重要城市,如安庆、南京,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,因此就算是身处北京的居民也感到不安,金融恐慌也就发生,银价开始大幅度跌落。清廷为了筹集军费,除了下放赋税权力之外,也滥铸减重的小制钱,导致通货膨胀。 总结来说,日记中所记录的关于银钱兑换的情况,反映了咸丰时期的战争与银价的下跌有密切的关系,其次战争也破坏了当时的商品经济,使货币流通规律产生了变化。 《王锺霖日记》一书主要收录了王锺霖自咸丰八年到咸丰十一年的日记,从中可以窥见晚清社会风貌。 《王锺霖日记》中所载史事,多是作者细心观察之后的记录,史料价值很高,既可以证史,也可以补史,可以作为晚清历史研究的文献资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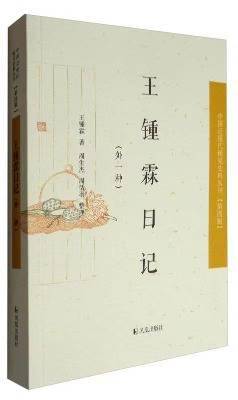 《王锺霖日记(外一种)》,王锺霖著,周生杰、周恬羽整理,凤凰出版社出版 缺水的北京 日记对当时北京的供水情况作了一个很详细的描写。自古以来,人类用水的源头主要来自雨水、地面水和地下水,最适合公共使用的水源为地面水,其次是地下水,最后是雨水,但雨水不稳定。除此之外,在地面水方面,也是缺乏的,“近郊二十里,无河流灌润”, 因此北京居民在日常用水方面较为依赖地下水,即井水。 北京人口稠密,用水量大,但是供水的措施并不发达。“北京的井多在街上,除了王公之家,极少在自家宅院凿井。街上水井系卖水者所有,故市人常自卖水者手中买水。”除了甜水井是自行用车去取之外,其余的井水都是通过水屋的工人去运输,按日记中叙述,经营水屋的均是山东登州人,送水的工作十分辛苦,需风雨无阻地送到各家,突出了山东人的辛勤。而水屋的经营范围也有明确的划分,不同水屋有着不同的送水范围,互不侵犯,这种分段经营的方式早在乾隆年间已经开始定下来。“从乡缘的角度,这种分段把持的经营方式,或许也是同乡之间彼此的互利措施,也就是山东人基于‘有饭大家吃’的乡谊,产生了这种联合垄断的方式。”通过日记可以看出,这种同乡情谊虽然是建立在利益之上,但是乡里有困难,水屋的其他同乡也会伸出援手,用平常积累下来的公款,帮助有需要的人,可以说是十分有人情味。 频繁变动的物价 晚清动荡不安,除了吏治败坏,在经济方面也十分不稳定,通过货币的浮动就可以看出。货币的价格浮动幅度非常大,而且速度很快,同一天的早晚银价就有所变动,可见晚清时期政府对于银价的控制十分薄弱,食物的价格高昂,换而言之就是百姓可能面临饥饿,而市井商人则从中获利,市场出现失衡。 经济不稳定的情况持续了一段长时间,王锺霖在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了银价波动的情况。咸丰十年(1860),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,百姓欲逃往其他地方避难,纷纷到钱铺取钱,部分私人钱庄的老板早已弃铺而逃,百姓只能到官号取钱,但官号储备金钱不够,只好能拖则拖。除了米面菜蔬这些必需品之外,衣物也已经不值钱,市道萧条,顾客稀少。除此之外,当铺也是货物满架,并且此时是有当无赎,因为当铺已经出不起高价,所以市民只好把自己的物件低价当给当铺。 战争和灾荒会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变成货币,用货币购买粮食,越来越多的贵金属流入市场,形成供大于求的情况,这样一来使得货币的需求增加,银价会下跌。由于太平军连续攻克了重要城市,如安庆、南京,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,因此就算是身处北京的居民也感到不安,金融恐慌也就发生,银价开始大幅度跌落。清廷为了筹集军费,除了下放赋税权力之外,也滥铸减重的小制钱,导致通货膨胀。 总结来说,日记中所记录的关于银钱兑换的情况,反映了咸丰时期的战争与银价的下跌有密切的关系,其次战争也破坏了当时的商品经济,使货币流通规律产生了变化。 《王锺霖日记》一书主要收录了王锺霖自咸丰八年到咸丰十一年的日记,从中可以窥见晚清社会风貌。 《王锺霖日记》中所载史事,多是作者细心观察之后的记录,史料价值很高,既可以证史,也可以补史,可以作为晚清历史研究的文献资料。
《王锺霖日记(外一种)》,王锺霖著,周生杰、周恬羽整理,凤凰出版社出版 缺水的北京 日记对当时北京的供水情况作了一个很详细的描写。自古以来,人类用水的源头主要来自雨水、地面水和地下水,最适合公共使用的水源为地面水,其次是地下水,最后是雨水,但雨水不稳定。除此之外,在地面水方面,也是缺乏的,“近郊二十里,无河流灌润”, 因此北京居民在日常用水方面较为依赖地下水,即井水。 北京人口稠密,用水量大,但是供水的措施并不发达。“北京的井多在街上,除了王公之家,极少在自家宅院凿井。街上水井系卖水者所有,故市人常自卖水者手中买水。”除了甜水井是自行用车去取之外,其余的井水都是通过水屋的工人去运输,按日记中叙述,经营水屋的均是山东登州人,送水的工作十分辛苦,需风雨无阻地送到各家,突出了山东人的辛勤。而水屋的经营范围也有明确的划分,不同水屋有着不同的送水范围,互不侵犯,这种分段经营的方式早在乾隆年间已经开始定下来。“从乡缘的角度,这种分段把持的经营方式,或许也是同乡之间彼此的互利措施,也就是山东人基于‘有饭大家吃’的乡谊,产生了这种联合垄断的方式。”通过日记可以看出,这种同乡情谊虽然是建立在利益之上,但是乡里有困难,水屋的其他同乡也会伸出援手,用平常积累下来的公款,帮助有需要的人,可以说是十分有人情味。 频繁变动的物价 晚清动荡不安,除了吏治败坏,在经济方面也十分不稳定,通过货币的浮动就可以看出。货币的价格浮动幅度非常大,而且速度很快,同一天的早晚银价就有所变动,可见晚清时期政府对于银价的控制十分薄弱,食物的价格高昂,换而言之就是百姓可能面临饥饿,而市井商人则从中获利,市场出现失衡。 经济不稳定的情况持续了一段长时间,王锺霖在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了银价波动的情况。咸丰十年(1860),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,百姓欲逃往其他地方避难,纷纷到钱铺取钱,部分私人钱庄的老板早已弃铺而逃,百姓只能到官号取钱,但官号储备金钱不够,只好能拖则拖。除了米面菜蔬这些必需品之外,衣物也已经不值钱,市道萧条,顾客稀少。除此之外,当铺也是货物满架,并且此时是有当无赎,因为当铺已经出不起高价,所以市民只好把自己的物件低价当给当铺。 战争和灾荒会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变成货币,用货币购买粮食,越来越多的贵金属流入市场,形成供大于求的情况,这样一来使得货币的需求增加,银价会下跌。由于太平军连续攻克了重要城市,如安庆、南京,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,因此就算是身处北京的居民也感到不安,金融恐慌也就发生,银价开始大幅度跌落。清廷为了筹集军费,除了下放赋税权力之外,也滥铸减重的小制钱,导致通货膨胀。 总结来说,日记中所记录的关于银钱兑换的情况,反映了咸丰时期的战争与银价的下跌有密切的关系,其次战争也破坏了当时的商品经济,使货币流通规律产生了变化。 《王锺霖日记》一书主要收录了王锺霖自咸丰八年到咸丰十一年的日记,从中可以窥见晚清社会风貌。 《王锺霖日记》中所载史事,多是作者细心观察之后的记录,史料价值很高,既可以证史,也可以补史,可以作为晚清历史研究的文献资料。

